◎本报特约撰稿 李天庆
北宋时期的李格非,虽然品学双杰,著作等身,而后人对他的认识,却是缘于他的两个身份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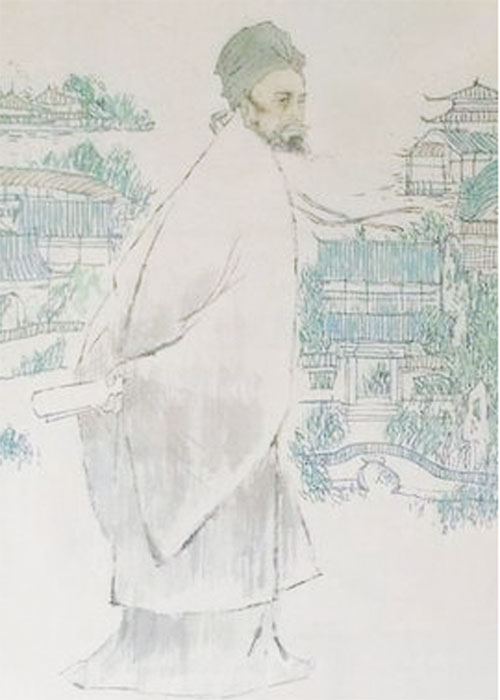
李格非
苏东坡的学生。李清照的父亲。
其实,李格非还是李清照这位词国女皇的终身教授。因为,李格非渊博精深的学识与典雅高贵的性情,正是造就这位五千年第一才女的文化基因。
今人可见的李格非作品,早已凤毛麟角。近日,本人翻阅冯惟讷主编的《嘉靖·青州府志》,偶见李格非七言绝句《过临淄》。而在其他文献之中却未见过,故此令人倍加珍惜:
《过临淄》
击鼓吹竽七百年,
临淄城阙尚依然。
如今只有耕耘者,
曾得当时九府钱。
“击鼓吹竽”是李格非对临淄人当年幸福美好生活的描述。
“九府钱”是姜尚封于临淄时铸造的齐国钱币。
全诗是李格非路过齐国故都之时,触景生情而引发的感慨。他想到齐都当年的“击鼓吹竽”,势必也会想到《战国策》所说的盛况:“临淄之途,车毂击,人肩摩,连衽成帷,举袂成幕,挥汗成雨。家敦而富,志高而扬。”然而,那个赫赫扬扬700年的豪华存在,而今早已散为云烟,荡然无存,只有一座“城阙”茕茕孑立,形影相弔。而随着车马红尘一起消逝的,不仅是“连衽成帷”的人流及其“志高而扬”的自信,便是古城内外那喧嚣街市与宽阔道路,如今也转化为庄稼地,专供农人“耕耘”了。
于是,这座“尚依然”的旧城,就像一个巨大的黑箱,收藏了人们急于知晓的秘密——为什么花锦世界也会转瞬即逝?为什么雄齐大都也要回归农田?这是葬礼后的沉寂,还是凯旋后的淡然?如此凝重的,甚至滴着血泪的惊叹与天问,又为什么无人顾及,无人关心?
李格非以其明心慧性,终于找到答案:“曾得当时九府钱”。原来,钱是昌盛之基,钱是衰败之源。因为人们贪得无厌,为富不仁,又裘马声色,穷奢极欲,所以,再长远再美好的万紫千红,最终也必然落叶归根。
或许,李格非更加痛心的是,相距一千多年的齐国后人、大宋臣民,所注重所追寻所感兴趣的,依然是“曾得”那枚“九府钱”。而齐国的高节厚德,却与“耕耘”一概无关。这是岁月的轮回,还是人性的天然?此刻的李格非,大约只有忧心如焚了。因此,这首绝句的标题,就应该是《洒泪过临淄》。
当然,李格非这种人是不会仅限于想一想,说一说的,他是知而有行,知行合一的。他做郓州(今山东东平)教授时,薪水微薄,生活拮据。他的上级领导就想给他一个实惠的兼职,让他再挣一份。这可是天上掉下的大饼。然而,李格非却直接就对那好心的上级“谢不可”(《宋史》):谢绝而说不可以这样做。
他对九府钱并不痴迷。
与此同时,这种清雅淡泊的人生观,竟然立体化地默传潜移于李清照了。所以,李清照新婚不久,与赵明诚同游相国寺(类似后来的商城),却囊中羞涩,她就拿一件衣服典当了,“取半千钱,步入相国寺,市碑文果实。”(李清照《金石录后序》)她不仅没有埋怨丈夫窝囊,反而回家后“相对展玩咀嚼,自谓葛天氏之民也”(同上),就是两个人欣赏着拓片,品尝着水果,还自称是上古时代最快乐的人。
李清照回到青州归来堂的后期,赵明诚出仕有了俸禄,家中自然宽裕起来。李清照却依然不做阔太太。她反而“食去重肉,衣去重采,首无明珠翡翠之饰,室无涂金刺绣之具。”(同上)她如同躲避污秽一般躲避着富贵荣华。或许李清照以为,朴实简洁,删华就素,才是最好的境界,而那种见利忘义、醉生梦死的人生,可能连一枚“九府钱”都不会留在麦田里。因此她对追名逐利之人,从来就没有瞧得起。她的《钓台》诗里说得很清楚:
巨舰只缘因利往,
扁舟亦是为名来。
往来有愧先生德,
特地通宵过钓台。
相传,汉代严光拒绝皇帝刘秀的高官任命,隐居桐庐(今属浙江省)江边垂钓。后人便对先生蔑视功名利禄的崇高风范,仰慕不已。

李清照
李清照说,大船都为谋利而去,小舟亦是沽名而来。先生的品德让他们惭愧,他们便趁着黑夜,从先生钓台下,小偷儿似的溜过去。
如果说,李格非的《过临淄》,是找到了社会凋残、文化衰败的根源,那么李清照的《钓台》,就是又看到了悲剧的重演。因此,想必李清照也是“含泪过钓台”的。
当然,李清照的知行合一,也是不折不扣的乃父之风。便是她的亲人利欲熏心,她照样不会虚美隐恶。且看她的《感怀》:
寒窗败几无书史,
公路可怜合至此。
青州从事孔方兄,
终日纷纷喜生事。
作诗谢绝聊闭门,
燕寝凝香有佳思。
静中吾乃得至交,
乌有先生子虚子。
这是李清照从青州到莱州官邸去看望赵明诚时所作。她说她远道而来之后,被安排在没有“书史”的“寒窗败几”之间。她随之又检讨自己,我来到官府了,怎么还奢望看到书史啊?这不是像汉末将军袁术(字公路)那样,身陷绝地之后还想喝一碗蜜汁吗?
“青州从事”是好酒,“孔方兄”是铜钱。
李清照说,知州大人赵明诚,此刻正乐此不疲地终日忙碌,忙着那无有休止的生计——喝酒,捞钱。
那就赶紧关上房门吧。摒绝了外面的浊气,室内自然也就“凝香”而有作诗的“佳思”了。在这宁静之中,李清照得到了一位至交好友,那就是子虚乌有,就是没有。
此时此刻,赵明诚的至交已经不是李清照,而是“青州从事孔方兄”,李清照的至交也不是赵明诚,而是超然于一切的虚,无,空。
在这里,李清照的“孔方兄”与父亲的“九府钱”,无意间就形成了神秘的“量子纠缠”。我想,由此而引发的心灵共振,足以在人们精神世界绕梁三日了罢。
至此,我们可能已经发现,李格非的《过临淄》,体现了诗人对齐国凝重历史的深刻反思,对大宋严峻现实的极度忧虑。因此,他眼前那座临淄城阙,既是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”的文化符号,又是一座长鸣的警钟,告诫人们——欲望,让人拥抱着幸福感,升华为过眼烟云——而真正听懂的,正是李清照,或者说只有李清照。
李格非《过临淄》中闪烁的宝贵的人格、高尚的价值取向和永恒的精神之光,多么像一粒丰满的种籽,在李清照这里长成了参天大树。正如冯蜂鸣所说:“李格非既是李清照的父亲,又是李清照这位文学家诞生的母亲。李格非深深影响于李清照的,是他那内旷外疏的一片冰心与拄笏看山的超然之气;灌输给李清照的,是他那言必有中的微言大义与识破天机的为文真谛。”(《冯蜂鸣解密李清照》)
今天,我们又通过李格非与李清照之间的文化DNA比对,明确看清了两者的高度相同,看清了父女二人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及其美学理念的源流相继,一脉相承。可见:
一个伟大的女儿背后,还有一个伟大的父亲。